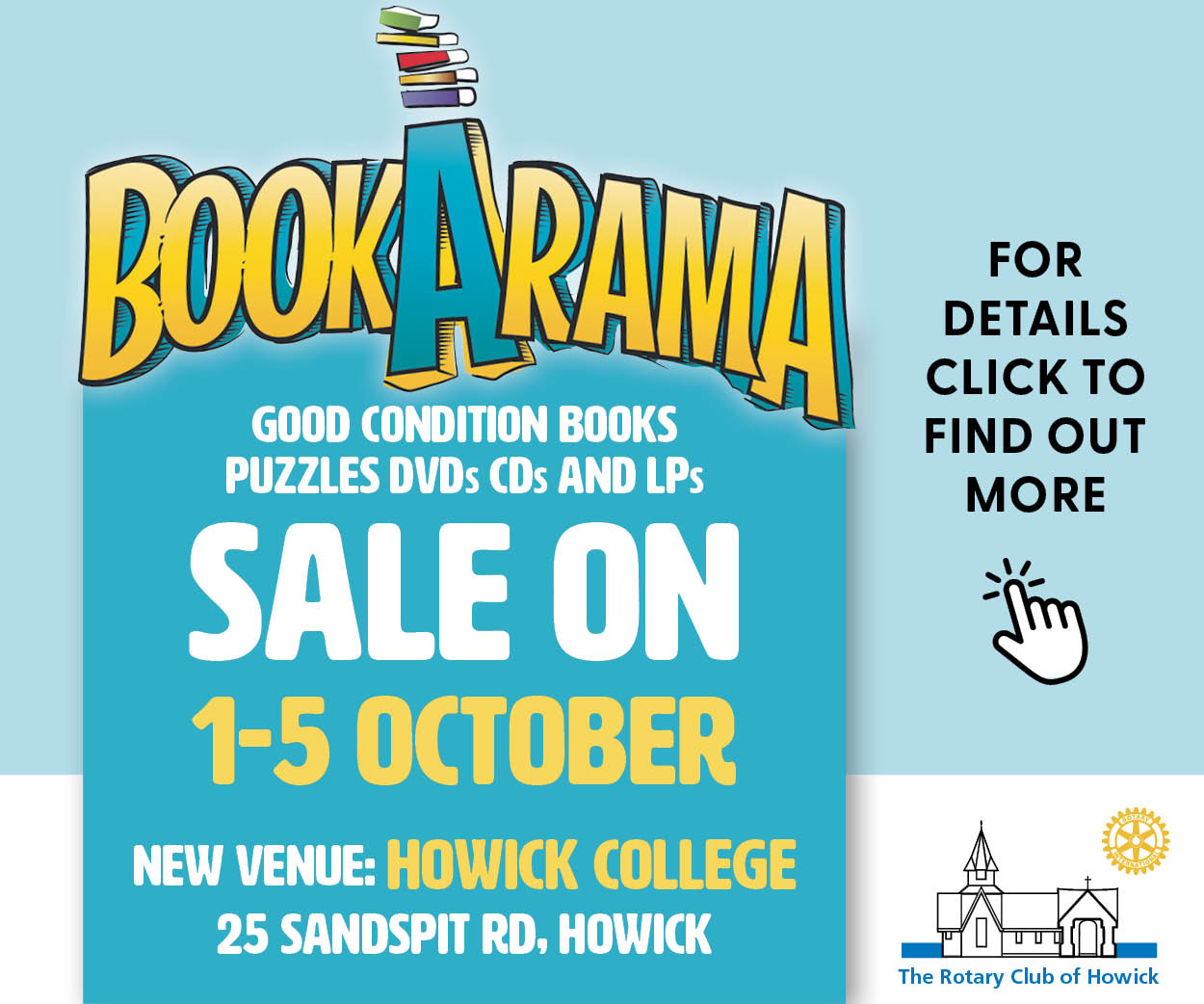克劳福德医疗中心(Crawford Medical Centre)在豪维克(Howick)和奥克兰东部社区享有盛名,许多市民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治疗。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领导着这家诊所,并向 PJ TAYLOR 讲述了他的一些医疗经历。
你在哪里出生和长大?
我出生在新西兰黑斯廷斯,父亲是一名果园主,为瓦蒂公司供应水果。这是一个成功的家族企业,我的父母、哥哥姐姐们都在普卡瓦的果园里一起工作,包装水果并运送到黑斯廷斯的工厂。父亲热爱这片土地,并为之倾注了大量精力。1951 年朝鲜战争期间,羊毛的利润很高,他被养羊的前景所吸引。他卖掉了果园,举家北迁,在旺格雷和达加维尔之间的胡托地区建立了一个牛羊养殖场。不幸的是,搬迁后不久,羊毛价格暴跌。北地农场本来就地少人多,受到重创,我们家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经济拮据。我们居住在 1000 英亩灌木丛生的农田上,很难使其具有生产力。生活艰难,资源匮乏。母亲经常为我们做衣服,我们也学会了用很少的钱维持生计。我是九个孩子中的一个,其中有两对双胞胎。最大的是我的哥哥扬(Jan)和姐姐朱迪丝(Judith),后来我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让我们学会了坚韧和机智。
我从提托基小学(Titoki Primary)开始上学,然后在提托基区中学(Titoki District High School)读到五年级。由于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我后来转到旺格雷男子中学(Whangarei Boys' High School)完成了最后两年的学业。我早年的生活深受农业、农村和毛利社区的影响。我学会了一些毛利语。这些联系对我来说仍然意义非凡。
另一个深远的影响来自我个人:小时候,我患上了严重的骨髓炎。我在旺格雷(Whangarei)的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接受手术和抗生素治疗。这段经历为我埋下了一颗想法的种子,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医生。生病之前,我是一个强壮活泼的孩子,喜欢打橄榄球、跑步,还获得过学校田径比赛的奖项。
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一名医生的?
在旺格雷男子中学,我因骨髓炎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决定要接受医生培训。我的哥哥蒂莫西选择了牙科,我们一起南下达尼丁。他进入了奥塔哥牙科学校,我则进入了奥塔哥医学院。
在但尼丁的几年是一个重大挑战。我在北地农村长大,那里的高等教育并不是重点,而我突然来到了一个远离家乡、要求苛刻的学术环境。起初,这让我望而生畏。我的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通常拥有专业或医学背景,而我的家境则要殷实得多。这种反差让我很难适应,但也促使我去适应,变得独立,并找到自信。最终,这些年锻造了我的韧性和决心,让我顺利完成了医学培训,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成长。
在达尼丁的奥塔哥大学接受医生培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但尼丁的第一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来自旺加雷(Whangārei),出身农家,却与来自专业家庭的年轻人打成一片,其中有些人很富有,甚至拥有自己的汽车。我从一辆自行车开始。第一年,即医学中级班,极具挑战性。要想进入医学院学习,竞争非常激烈。许多考生都是第二次参加考试,有些人已经完成了其他大学学位的学习,这让他们多了一次参加医学中级考试的机会。
当时只有 130 个名额,其中一些名额是专门分配给毛利学生的。根据记忆,大约有 600 或 700 名学生参加了考试。我很荣幸地通过了考试,并获得了医学培训课程的录取名额。医学院的第一年又是艰难的,因为我的学校教育中没有生物课。我必须快速学习化学基础知识,如硫酸铜晶体的性质,并进行实验室练习,如青蛙剔骨实验。很快,我们就开始学习人体解剖学,并解剖捐赠给医学院的尸体,这既让人肃然起敬,又引人入胜。
尽管学习曲线很陡峭,但我在但尼丁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适应之后,我发现了新的活动和友谊,如徒步旅行、划独木舟和钓鱼。在个人成长的同时,我还获得了医学学位,并于1969年毕业。

您第一次来奥克兰东部是什么时候?
1969 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我在陶朗加医院度过了担任住院医生的第一年,并在那里结识了我的妻子桑德拉。培训的第二年我去了米德尔莫尔医院,之后我开始专攻麻醉学,并在格林兰产科医院工作了很长时间。这是一次宝贵的培训,但我最终意识到,麻醉学并不是我想从事的职业。之后,桑德拉和我花时间仔细考虑了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想在哪里定居。我们考虑过搬到北岛中部的尼尔森或奥克兰。最终,我们有幸在奥克兰东部找到了一个机会。1972 年,我从 Daphne 和 Hugh Holroyd 医生手中买下了豪维克的一家全科诊所。我开始独自开业,多年来,这家诊所稳步发展,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克劳福德医疗中心,继续为当地社区提供服务,与早期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
克劳福德医疗中心是豪维克皮克顿街景观带上一幢历史悠久、广为人知的诊所和建筑。您能解释一下它与该地区的联系和历史吗?
豪维克的老居民们一定还记得莱斯购物中心的那栋红砖小楼,它位于主街道的后面,休-霍罗伊德医生和达芙妮-霍罗伊德医生曾在那里行医,在他们之前,吉布森医生也曾在那里行医。我成为了那座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楼里的第三位全科医生。虽然古色古香,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它也变得狭窄、陈旧,越来越不适合我想要提供的医疗服务。
当时,澳新银行看中了这块地皮。时任当地银行经理的彼得-弗洛伊德(Peter Floyd)代表澳新银行找到我,表示他们希望在我们医疗室所在的土地上建立一家分行。虽然这意味着要离开那些熟悉的砖块,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理想的机会。那时,我已经准备好 "展翅高飞",建造更大、更现代化的建筑。经过协商,澳新银行同意买断我的租约,并协助我购买新的房产。
我一直很喜欢皮克顿街 4 号,这座房子与克劳福德家族以及豪维克和东部公共汽车公司有着悠久的渊源。1979 年,一直住在这里的博伊德一家准备搬走。博伊德先生是一位知名人士,曾担任豪维克市副市长,后来去世了,博伊德夫人决定卖掉房子。这让我有机会买下了这处房产,并将我的个人诊所搬进了后来成为克劳福德医疗中心雏形的地方。
这座建筑本身是一座古老的木屋,曾经是克劳福德一家的家。据我所知,公交车司机在深夜返回时,有时会先在这里睡上一觉,第二天再回到自己的线路上。多年来,博伊德家族的成员偶尔会回到皮克顿街 4 号,要求在他们成长的房间里走一走,回忆一下他们的家。这种记忆的连续性--将克劳福德、博伊德和医学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使该遗址在豪维克的地方历史中占据了根深蒂固的地位。
20 世纪 70 年代的医学与今天的医学大相径庭。回想起来,全科医生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要容易得多,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受到很大限制。所有病人的病历都保存在一张 A5 的卡片上,问诊记录通常只有一行,还有一份处方清单。医学信息来自教科书,以及我早年在公立医院系统担任学生和家庭外科医生的经验。
作为一名独立的全科医生,我没有任何支持,几乎无法获得最新信息,也没有持续培训。回想起来,我对我们的管理能力感到惊讶。实验室检查很少。血液化验报告通常会在一周到十天后送到,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然后我们再用胶带粘在一张 A4 纸上。X 光和专科报告也是如此。等全科医生拿到这些信息时,有时已经过时了。记录保存非常繁琐,检索以前的信息往往也不可靠。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计算机刚刚问世,我就意识到这是唯一的出路。当我把诊所搬到皮克顿街 4 号,并聘请了一名助理医生时,我投资购买了全科诊所最早的计算机系统之一。1983年,一台个人电脑和一台打印机的成本是$24,000。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现在,人们可以即时获取信息,与医院和专家的沟通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教科书也已成为过去式。然而,患者的期望也随之改变。过去,患者可以在 7 到 14 天内得到最新信息,而现在,他们希望在 24 小时内得到答复。现在,大多数检查都是第二天出结果,全科医生必须随时准备立即采取行动。
几十年来,全科医学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病人护理无疑变得更好、更安全、更快捷,但从业人员的压力也大大增加。

您是如何参与在奥克兰东部创建下班后医疗服务的?
20 世纪 70 年代,豪维克的下班后服务仅由三名当地全科医生提供:罗伯-索本医生(Dr Rob Thorburn)、迈克-库珀医生(Dr Mike Cooper)和我。我们实行一对三轮班制,即每隔三个晚上,我们中的一人就会全权负责所有下班后和紧急护理工作。这往往意味着要在半夜和周末亲自接听电话。有时,一位母亲会在深夜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我家。虽然这并不理想,但往往是最快捷的解决方案,让我能够提供护理,然后回去休息。
最终,豪维克的下班后服务与帕库兰加的全科医生合并。我们在豪维克主街上的普伦凯特房间开设了夜间和周末诊所。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因为病人知道了晚上和周末去哪里就诊。随着医生团队的扩大,我们的办公场所不敷使用,于是搬到了阿伯菲尔迪大道,开设了第一家规模更大的下班后诊所。
在布雷特-海兰德(Brett Hyland)医生的远见卓识和领导下,诊所最终搬迁到了植物园路 260 号,并在那里继续运营。这项服务后来被称为 "东部护理急症室",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多年来,该机构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运营。然而,由于亏损,大约10年前,马努考地区卫生委员会撤销了对该中心的拨款,因此该中心的服务时间缩减为每天上午7点至晚上10点30分。
政府最近承诺提供资金,东部医疗中心有望再次全天候运营,为社区提供应有的紧急医疗服务。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与那些在下班后独自值班的夜晚相比,这项服务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几十年来,您一直热衷于航海。您在游艇领域做了哪些工作?
我一直热衷于运动,对帆船的热爱始于我在陶朗加医院担任内科医生期间。我的岳父是一位热衷于帆船运动的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陶朗加港周围航行,并航行到外面的岛屿。
搬到奥克兰后,我对游艇运动的热情依然不减。我驾驶小天使号帆船,并结识了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他是该级别帆船的世界冠军,经营着一家成功的造船企业。通过我们的友谊,我参与了新西兰 470 级帆船的开发。史蒂夫将第一艘 470 进口到新西兰并卖给了我,这艘船成为了他在当地生产的模型。后来,我又从他那里买了一艘 470 帆船,并参加了比赛,甚至驾驶这艘船参加了奥运选拔赛。
后来,我开始参加龙骨船比赛,并为自己建造了一艘法尔 11.6 米长的龙骨船,取名为 Titoki。当这艘船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时,我又购买了一艘新的法尔 11.6 米帆船,它更快、更轻、更强,更适合竞技比赛。在那些年里,我在豪维克帆船俱乐部、巴克兰兹海滩游艇俱乐部、新西兰皇家游艇中队和阿卡拉纳游艇俱乐部成功举办了帆船比赛。我曾五次前往斐济,将比赛和巡航结合在一起。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和兴趣的变化,我逐渐把注意力从航海转移到另一个爱好上:高尔夫,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喜欢高尔夫。
如果您希望新西兰社会有什么变化,会是什么?
作为一名医生和一家医疗中心的所有者,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难以招聘、培训和留住全科医生。多年来,选择从事全科工作的年轻医生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我们越来越依赖海外培训的医生。虽然这些医生中有许多人表现出色,但也有一些人一开始很难适应新西兰的医疗体系。过去的 "家庭医生 "模式,即全科医生的工作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似乎已基本不复存在。现在,很少有全科医生能够像过去那样长期投入工作,而这正是人们所期望的,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从患者的角度来看,我很希望看到全科医生在基层医疗机构安家落户,终生从事这一职业,并与家庭建立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跨越几代人。如今的全科医生已大不相同,我不确定旧模式是否会完全重现,但我希望能鼓励全科医生和患者都能从中受益。